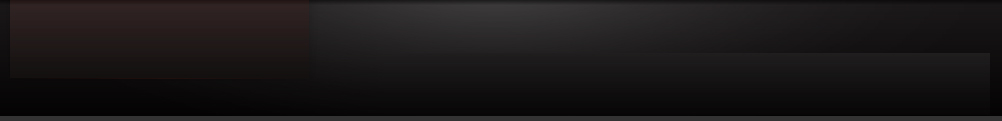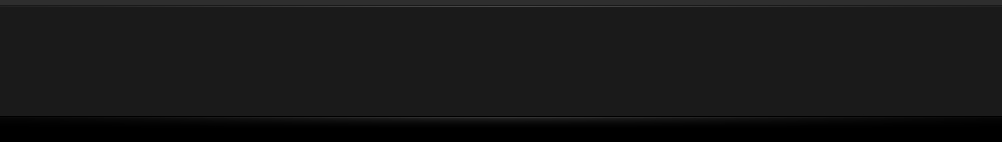山东飞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电 话:0635-8579856
0635-8579857
手 机:13863588378
传 真:0635-2996665
Q Q:397366996
联系人:韩经理
电 话:0635-8579856
0635-8579857
手 机:13863588378
传 真:0635-2996665
Q Q:397366996
联系人:韩经理
中国经济新信号:消费对经济增长驱动力快速提高
作者:admin 发布于:2013-6-19 11:52 Wednesday
据《济南证券报》报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7月份的消费增长率为12.7%。这样中国的消费增长率已经连续16个月增长速度超过12%。在投资和外贸增长动力开始减弱,趋势开始下降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能保持相对较高和稳定的增长速度,那它意味着中国的消费存在着脱离投资周期而走出独立向上的稳定增长周期,其结果必然是中国的消费率存在快速提高的可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驱动力量将逐渐提高。
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成熟行情经济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赶超型、发展型和传统计划体制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在较长时期内还难以改变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如果消费率能适度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能不断加强,那么消费在支撑和平抑投资周期,引导资源配置效率,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等方面的作用会逐渐凸现出来。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居民的储蓄率始终在40%左右。高储蓄是中国经济获得高增长的基本保障。高储蓄使得基本依靠内部资金就能获得高速度的投资增长,不会像拉丁美洲诸国那样,要高投资就必须要高外债,最后又因外债危机而导致经济危机。
高储蓄并且储蓄资金主要以银行信贷形式提供给投资者,使得中国的投资效率虽然不高,甚至存在很多无效投资,但是这些低效和无效的投资,只会表现为银行不良贷款和呆坏账的不断增加,不会导致对外负债中不良资产的增加。
储蓄不等于投资,储蓄并不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消费主体和投资主体分别决策,受各自独立的因素驱动。储蓄和投资的平衡要靠金融行情和利率体系来完成。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始终是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直接经济根源。中国储蓄率的相对稳定性使得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始终是投资,以保障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适应储蓄率。中国的高储蓄率决定着高投资增长率是常态。因此,即使是正常的投资增长率也要远高于GDP的增长率。否则,经济循环中肯定会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
如果说在过去的几轮高增长周期中,突出的矛盾是传统体制下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高投资增长与储蓄之间的矛盾,矛盾的结果是以通货膨胀形式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从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高增长凸现了另两大矛盾:高投资所形成的产能(跟投资效率提高有关)与有限的消费需求的矛盾;投资高增长所形成的能源原材料需求与原有的能源原材料供应模式的矛盾。而过去出现的投资高增长必然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的现象并不突出。
这两大矛盾最终都表现为上游行业产能快速扩张和市场飞涨,下游行业成本压力增大和行情需求紧缩依旧的矛盾。上下游产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容易使经济出现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的滞胀。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在缓解和部分解决这两大矛盾的基础上才能使投资重新步入高增长的轨道,否则就只能将投资增速降下来。
如何保持消费较快增长,逐步提高消费率;如何适应中国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的需要形成新的能源原材料供应模式,解决能源原材料瓶颈问题,是今后宏观调控的两大核心任务。
中国居民的收入现金流不稳定,工作环境变化大。中国居民收入虽然在快速增加,但是居民间收入差距在拉大,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在不断降低。这些都是解释中国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很好的理由。问题是二十多年来,上述因素难道不在变化之中?血缘观念在削弱,居民收入在增长,社会保障制度在完善,为什么居民消费率就没有什么变化呢?
反观日本、韩国等文化背景相近的诸国,也有过高储蓄的阶段。但是随着经济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都曾经历过居民消费率快速上升的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在日本的重工业化阶段,居民储蓄率也曾在38%左右,到八十年代储蓄率开始快速下降。目前,日本的储蓄率只有28%左右。尽管远远高于欧美国家,但是储蓄率毕竟下降了30%左右。
因此,光从文化观念和制度角度去认定中国高储蓄会长期持久下去是站不住脚的。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也会出现消费率快速上升的阶段,而且中国距离这样的阶段已经为时不远。如果达到这样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逐渐从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增长的动力和产业增长格局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仅仅从连续16个月的消费高增长还无法推论出中国居民的消费偏好已经在快速提高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制约居民消费的因素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首先,从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高增长,是基本无通胀下的高增长,是所有非再生资源价值的大发现(表现为所有非再生资源市场的刚性上涨)。高增长不仅仅给居民带来了劳动收入(工资奖金)的增长,更给拥有非再生资源的居民带来了资本要素收入上的增长。前者是可统计的,后者是不可统计的。因此,这几年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要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为今后几年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其次,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制约即期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经过住房制度改革和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国居民住房的私有化率达到76%,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经接近25平方米,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住房需求的不确定性。尽管,住房信贷在短期内会抑制即期支出,但是经过几年后,住房问题的解决会刺激人们的即期消费。
第三,受传统观念约束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居民目前基本处于退休年龄,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的居民正在成为收入和消费主体,他们的消费观念跟前辈有很大的不同,即期消费倾向高,消费信贷意识强。这些特色已经可以从这一轮房地产和汽车消费热中充分体现了出来。量变会引起质变,上述条件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居民消费倾向的提高。
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成熟行情经济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赶超型、发展型和传统计划体制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在较长时期内还难以改变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如果消费率能适度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能不断加强,那么消费在支撑和平抑投资周期,引导资源配置效率,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等方面的作用会逐渐凸现出来。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居民的储蓄率始终在40%左右。高储蓄是中国经济获得高增长的基本保障。高储蓄使得基本依靠内部资金就能获得高速度的投资增长,不会像拉丁美洲诸国那样,要高投资就必须要高外债,最后又因外债危机而导致经济危机。
高储蓄并且储蓄资金主要以银行信贷形式提供给投资者,使得中国的投资效率虽然不高,甚至存在很多无效投资,但是这些低效和无效的投资,只会表现为银行不良贷款和呆坏账的不断增加,不会导致对外负债中不良资产的增加。
储蓄不等于投资,储蓄并不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消费主体和投资主体分别决策,受各自独立的因素驱动。储蓄和投资的平衡要靠金融行情和利率体系来完成。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始终是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直接经济根源。中国储蓄率的相对稳定性使得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始终是投资,以保障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适应储蓄率。中国的高储蓄率决定着高投资增长率是常态。因此,即使是正常的投资增长率也要远高于GDP的增长率。否则,经济循环中肯定会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
如果说在过去的几轮高增长周期中,突出的矛盾是传统体制下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高投资增长与储蓄之间的矛盾,矛盾的结果是以通货膨胀形式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从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高增长凸现了另两大矛盾:高投资所形成的产能(跟投资效率提高有关)与有限的消费需求的矛盾;投资高增长所形成的能源原材料需求与原有的能源原材料供应模式的矛盾。而过去出现的投资高增长必然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的现象并不突出。
这两大矛盾最终都表现为上游行业产能快速扩张和市场飞涨,下游行业成本压力增大和行情需求紧缩依旧的矛盾。上下游产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容易使经济出现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的滞胀。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在缓解和部分解决这两大矛盾的基础上才能使投资重新步入高增长的轨道,否则就只能将投资增速降下来。
如何保持消费较快增长,逐步提高消费率;如何适应中国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的需要形成新的能源原材料供应模式,解决能源原材料瓶颈问题,是今后宏观调控的两大核心任务。
中国居民的收入现金流不稳定,工作环境变化大。中国居民收入虽然在快速增加,但是居民间收入差距在拉大,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在不断降低。这些都是解释中国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很好的理由。问题是二十多年来,上述因素难道不在变化之中?血缘观念在削弱,居民收入在增长,社会保障制度在完善,为什么居民消费率就没有什么变化呢?
反观日本、韩国等文化背景相近的诸国,也有过高储蓄的阶段。但是随着经济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都曾经历过居民消费率快速上升的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在日本的重工业化阶段,居民储蓄率也曾在38%左右,到八十年代储蓄率开始快速下降。目前,日本的储蓄率只有28%左右。尽管远远高于欧美国家,但是储蓄率毕竟下降了30%左右。
因此,光从文化观念和制度角度去认定中国高储蓄会长期持久下去是站不住脚的。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也会出现消费率快速上升的阶段,而且中国距离这样的阶段已经为时不远。如果达到这样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逐渐从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增长的动力和产业增长格局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仅仅从连续16个月的消费高增长还无法推论出中国居民的消费偏好已经在快速提高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制约居民消费的因素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首先,从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高增长,是基本无通胀下的高增长,是所有非再生资源价值的大发现(表现为所有非再生资源市场的刚性上涨)。高增长不仅仅给居民带来了劳动收入(工资奖金)的增长,更给拥有非再生资源的居民带来了资本要素收入上的增长。前者是可统计的,后者是不可统计的。因此,这几年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要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为今后几年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其次,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制约即期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经过住房制度改革和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国居民住房的私有化率达到76%,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经接近25平方米,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住房需求的不确定性。尽管,住房信贷在短期内会抑制即期支出,但是经过几年后,住房问题的解决会刺激人们的即期消费。
第三,受传统观念约束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居民目前基本处于退休年龄,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的居民正在成为收入和消费主体,他们的消费观念跟前辈有很大的不同,即期消费倾向高,消费信贷意识强。这些特色已经可以从这一轮房地产和汽车消费热中充分体现了出来。量变会引起质变,上述条件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居民消费倾向的提高。